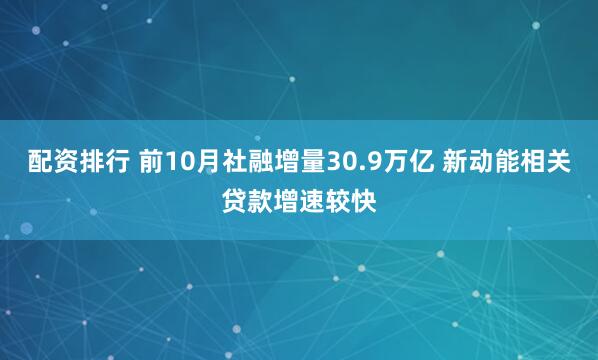“务必在半个月内找到牛宝正!”1950年11月5日清晨配资排行,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的值班电话突然炸响,传来的命令简短却不容置疑。听筒刚放下,办公室里已是一片忙乱:人事处调档案,公安厅派线人,交通厅则为可能的远途奔波做准备。谁也没想到,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寻人行动就此拉开帷幕。

负责协调的年轻干部张学德很快意识到难度。山东人多地广,“牛宝正”这三个字在居民登记册上并不稀奇。更棘手的,是中央文件里只给了一个模糊线索——“曾任北平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”。张学德暗暗琢磨:国民党旧狱警如今要么隐姓埋名,要么已遭肃清,如果他真在山东,还得看运气。
转机出现在第三天。渤海老区一位退伍干部回忆,抗战期间曾听母亲提起“牛班长”,家在无棣县城外三里。“这个名字当时耳熟,”他拍拍脑门,“人不坏,还帮过共产党。”这一句“人不坏”让张学德警觉:看守能被老百姓记住,多半另有隐情。于是调查组直奔无棣。

档案显示,无棣县赵家洼一带确有“牛宝正”,现被列为“三类人员”,处于劳动管制阶段。县公安点头道:“确实有其人,不过身份复杂,得审慎核实。”张学德决定亲访。第一次见面,他用例行审查口吻开场,被对方淡淡应付;第二次,张学德提起北平草岚子四个字,牛宝正抬头,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定住,接着低声问:“你们到底是谁?”就在这一瞬间,张学德基本肯定自己找到的正是中央要找的那个人。
身份敲定后,故事的另一面才渐渐浮出水面。1931年秋,北平地下党遭严重破坏,薄一波、杨献珍等数十人接连被捕,关进草岚子监狱。狱中严刑逼供、暗无天日,但党支部仍悄悄建立学习小组,同时物色可以争取的看守。那个年月,看守多是穷苦兵痞,能读识字的不多。牛宝正恰恰是例外:参过北洋旧军,识几个大字,又当上班长。他的家境却窘迫,老母重病、兄弟无依,微薄薪饷捉襟见肘,这给了杨献珍等人接近的突破口。

最初的接触源于一封家书。牛宝正苦于文笔,央杨献珍代写。字不过百,却把孝子难尽孝的愧疚写得入木三分。信写成后,杨献珍递上自己节余的两块大洋:“孝心要紧,这钱算借,你回头还。”薄薄银晃在掌心,牛宝正没说谢,只是深深鞠了一躬。这一鞠,往后五年里,他先后为党组织带进书报、夹出情报,甚至暗中藏好一份印有监狱警备布置的图纸。同志们给他取了代号“OX”,取其“老黄牛”之意,干活沉稳少言。
1936年春,刘少奇主持北方局,密令营救草岚子全部在押党员。行动设计极为大胆:伪造保释令、调包押送车辆、沿途设接应点。关键环节便是“狱内人”,没有牛宝正出面拖延点名、篡改交接,整个计划根本无法实施。行动前夜,他低声对杨献珍说了八个字:“我尽力,你们快走。”简短却铿锵。营救成功后,薄一波被秘密护送到太原,而牛宝正却因“通共嫌疑”当即被押。若非中共外围救援及时,他很可能被处以极刑。
动荡年代,再忠诚的渠道也难保畅通。脱险后,牛宝正辗转回到故乡,投亲靠友度日,和党中央完全失联。解放后,被误划为“三类人员”,原因无非是他当过国民党看守。档案上仅一句“历史复杂”,却掩住了生死与共的五年。

1950年中央下令寻找,其实出自薄一波、刘澜涛、安子文三人联名。解放初接管草岚子旧址时,几位老同志谈及往事,同声提到“OX”。“欠他一声‘谢谢’不能再拖。”薄一波当场拍板:务必弄清生死,若在,立请进京;若殉难,抚恤其家。于是才有最初那通急电。
被告知中央“前功不忘”时,牛宝正先是愣住,随后喃喃一句:“我真没做啥大事。”言语朴素,却显出隐秘的自豪。他唯一的顾虑是年近花甲的老伴舍不得离乡。张学德当即表示:可先赴京安置,家属随后安排;中央还会妥善解决子女就业。听到这里,老兵颤着手签下同意书。

进京后,薄一波等人轮流登门。昔日囚徒与旧班长对坐一桌,气氛并不尴尬。薄一波端起茶碗,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老牛,你救的可不只是我个人。”礼遇也很实在:北京市公安局聘其为预审顾问,行政十八级;同时解决其独子工作编制。那年冬天,北京的暖气烧得极好,牛宝正常感叹:“身上热,心里更热。”
遗憾的是,好景并不长。1954年春,他因肺疾医治无效去世。丧礼从简,却有一块特别的挽联:“草岚义士,公仆精神。”家属遵照遗嘱将其骨灰送回无棣老坟,墓碑只刻姓名与生卒年,没有任何夸张称号。当地老人至今提起这座小坟,仍会补一句:“那可是救过薄部长的人。”

牛宝正的经历足够说明:革命胜利绝非单靠书本里的英雄,它还需要无数出身平凡、动机朴素却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的人。档案中写不尽人的情义,但那些被放大的细节——一封家书、两块大洋、一次拖延点名——往往决定了历史拐点的方向。说到底,功勋不在职位高低,而在选择。牛宝正当年选择了冒险帮忙,后来中央同样选择为他正名,这份互相成全,便是时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启示。
盛鼎管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